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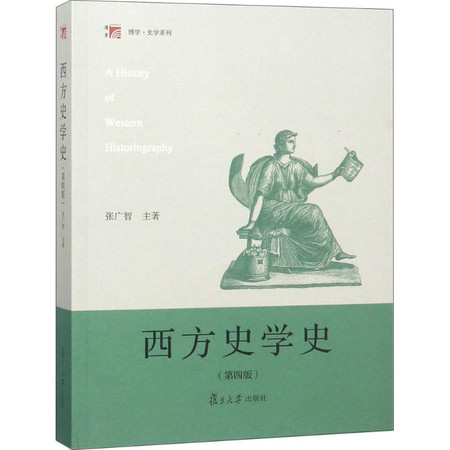
带来的巨大机遇和诸多挑战?这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实践问题。
1956年8月,美国科学家约翰·麦卡锡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夏季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一词,标志着AI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所谓“AI”,特指模仿人类智能行为的科学技术。数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深入发展和普及,AI理论与方法和实际应用迅速拓展。2022年底,ChatGPT正式对外发布,它在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等方面的出色表现,使人机对话更顺畅。2024年底,DeepSeek上线并同步开源,既支持“联网搜索”,也支持“深度思考”,强有力地激发中文世界使用AI的热情。
习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在世界大变局中,不仅世界经济版图已经被改写,世界力量对比也已发生历史性变革,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迅猛发展,正在加快重塑世界。而AI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慢慢的变成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
人类的文明史,某一些程度上可以看作科技革命的历史。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至少经历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先后进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自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技术与科学由彼此分离走向密切结合,科学越发成为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必要因素。马克思指出,“生产的全部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的全部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这样就“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飞跃。科学技术革命破坏旧世界,全面推动人类社会深刻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第一生产力。
唯物史观的基础原理之一,是强调历史不会发生彻底的断裂,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留下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蒸汽机是“动力引擎”。此前,除人力和畜力外,人类只能利用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动力。恩格斯指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广泛确立。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电气革命,又是一次“巨大的革命”,把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此时电力作为“通用能源”重塑世界。电力、化学、石油、汽车、钢铁、造船、采矿等重工业,成为主导工业。垄断代替“自由”竞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一般认为,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微型化,个人电脑大范围的应用,特别是互联网作为“连接载体”实现全球信息相互连通,对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智能时代,AI已经将信息时代的“连接”升级成“理解与决策”。这一升级具有划时代意义,表明AI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引擎,属于“元技术”——既是“通用技术”也是“基础设施”。它已经深入人类社会各领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AI+X”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加速走进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数智时代。
2016年,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们国家发展大历史中去看。”2021年,习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2023年,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再次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们国家社会发展、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习关于大历史观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因应数智时代机遇与挑战的根本遵循。
大历史观既不是研究内容在时空上的延伸,也不是史家主体意识在史学方法某一方面的彰显,而是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和历史辩证法的辩证统一,凸显历史矛盾运动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内在联系。大历史观至少提出三方面新的要求:主体性基础上的整体性要求、史学理论意义上的跨学科要求、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要求。三个方面彼此不可分割,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就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创新发展而言,上述三方面要求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当AI技术融入历史研究时,它可在“联网搜索”的基础上,提供海量信息,并整合多种形式的历史文献,在开放性、网络化、算法等支持下,就文献的收集、整理、释读、应用等,更快捷地向使用者提供智能对话、语义理解、逻辑推理、文本生成等“深度思考”。这一前提,使我们大家可以把社会历史的研究,纳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大系统中整体性考察。历史研究中原本分散、个别或断裂的历史现象,将成为“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避免乃至超越“碎片化”或者“假”的整体性研究。鉴于大数据在融合定量与定性数据方面的优势,AI有助于消除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定性与定量研究的隔膜,在准确性上提供切实保障。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深层次地融合,是促进广泛跨学科合作的必经之路。毋庸讳言,任何一个“大”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仅借助某个单一学科。整体性、跨学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大历史”,为解读人类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进一步提升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开辟新的广阔的现实道路。
2025年4月,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我们要“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们国家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导向”,首先就是要巩固、捍卫和发展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特性,是“两个结合”的结晶,是历史自信的强有力依托。有咋样的主体性,就有咋样的史学。史学主体性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历代中国史家以自己的责任、使命、学识、热情,甚至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它在史学发展中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不可替代。
面对AI,历史学家要巩固、捍卫和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AI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历史研究带来非常大机遇的同时,也提出诸多挑战。用好这把“双刃剑”,必须对如下重大理论问题有清醒认识。
其一,AI的本质是工具而非科研主体,科研主体是人,是有主体意识的人。必须正视大模型存在的“幻觉”现象。所谓“幻觉”,被认为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或表现为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捏造事实;或是生成内容与用户指令不一致,逻辑混乱,甚至南辕北辙;或是存在无法验证的所谓的“事实”。在历史研究中,若无视“幻觉”现象,即无视将虚构与真实无缝拼接的错误,科学价值则无从谈起。
其二,史家是现实的、理性的人,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抽象的“数字化存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在数智时代,历史学家依然是历史研究的主体,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在数智时代面临的挑战,不是AI发展之过,而是人类还没做好准备。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否认科学是一种革命力量,数智时代也是如此。问题的重点是人们如何顺应历史大趋势,切实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不能抛弃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在发挥AI技术优势的同时,保持史家理性思维的优势;在不断的提高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的同时,逐步的提升历史研究的效率和水平。
其三,通过不断巩固史学主体性、彰显史家主体意识,应对AI的冲击。这就要坚持理论上的守正创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融入历史认识的价值塑造,而不能用技术算法取代历史研究的价值判断,更不能用AI技术消解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放弃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面对AI的历史学,就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学科根基被动摇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我们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数智时代,这些教诲启迪我们进一步思考历史科学的重要性。历史学者拥抱AI,不仅要思考史学如何与AI共生,更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到,在AI时代如何坚守史学的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如何从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联系的大历史中弘扬历史精神,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智慧,不辜负这一伟大的时代!